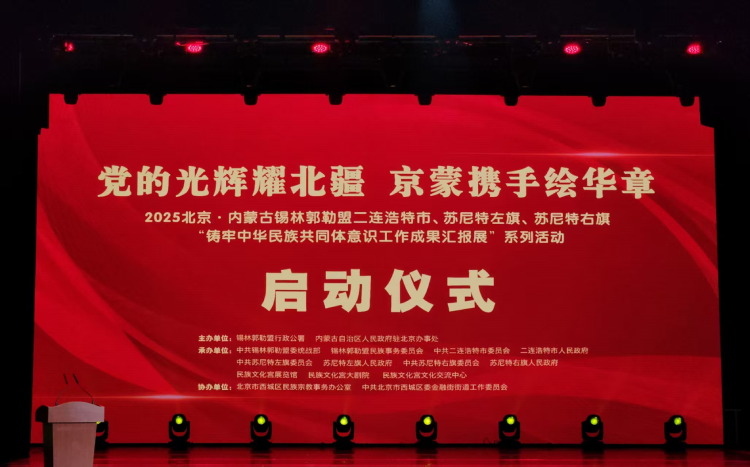这几天,南方的气温遭遇断崖式下跌,西北风将银杏树的叶片吹得纷纷扬扬,满地都是黄色的叶片,一树金黄的样子不见了,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;石榴树留下的几片残叶还顽强地挂在树梢,几只干瘪的小石榴在寒风中晃荡着,还想着留住已经逝去的秋天。一股寒潮袭来,夜里忽然飘起了雪花,一下子进入了速冻模式,虽然今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迟一些,但来得很猛,没有迟疑,说来就来了。
记得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更冷。
每年的秋收冬种结束以后,生产队总要利用冬闲时节安排修水利,主要是发动男女老少掘河泥。趁天气晴好,抽水机抽干河道的水,社员们从河底到河岸一字排开,接力递送泥浆和泥块。那时没有高筒靴,卷起裤腿,赤脚走向积水的河底,河中结着簿冰,试探着将一只脚伸进水里,忽觉一股寒流一下子直冲心底,立刻打了个寒战,咬咬牙又把另一只脚踩了下去……
天冷了,过去老屋的木门窗漏风,每到冬天来临之前,家家户户总会把窗户用尼龙纸糊好,以防西北风吹进屋里。
挑一个晴好的日子,当家人从柴蓬里拔几把早稻草(早稻草比晚稻草松软),用铡刀将早稻草铡成手指般长,一截一截的,晒在竹簟上,趁午后的暖阳收起来,装在一个粗布做的布套里,铺在床上保暖,闻着又有稻草的香味。
水缸周围护上稻草,用一根竹杠斜插在水缸里,防止水缸结冰破裂。
猪圈的围墙和房檐之间留出的空间,用竹杆和稻草扎好草帘子一层一层叠挂起来,挡住吹来的寒风。给菜地里的萝卜和黄芽菜披上尼龙簿膜,以防雨雪冰冻。
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熬。如果北方的冬天是干冷的话,那么南方的冬天就是给人一种湿冷的感觉,由于南方的湿度大,这种感觉是深入骨髓的。家里没有生火和暖气,晚上睡觉,脱了棉袄棉裤,盖在被子上,用手压一个压,钻进冰凉的被窝里蜷缩着身子,好长时间才能暖过身来。有时候后半夜醒来,却迟迟下不了起来方便的决心。早晨起来,要穿冰凉的棉袄棉裤,怕冷懒在床上。棉袄棉裤在灶间烘过后,起床就容易些,尤其是棉鞋,在火熜上烘过,热热的穿进去舒服多了。
早上起来水缸里结着厚厚的冰,一根竹杠冻住了,碰碰它,一动也不动。湿毛巾被夜里的冰塑了型,硬邦邦的立在脸盆里,只得用热水瓶里的热水冲软,再舀一勺灶台上的汤罐水洗洗脸。端着一碗年糕泡饭,放点猪油和酱油,那是最美味的早餐。
]
戴上口罩,迎着刺骨的寒风,走在结冰的路上去上学,浑身冻得瑟瑟发抖,牙齿也会打架,两只耳朵像刀割一般。坐在前面的小伙伴,一不小心,两脚一滑,仰天一跌,后面的小伙伴赶紧上前把他搀扶起来,他咧着嘴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。
教室里的温度跟室外差不多,北面的玻璃窗不知是哪个捣蛋鬼用石头扔破的,尼龙纸没有糊严实,一股冷飕飕的北风从缝隙吹入教室,十分阴冷。红通通的手冻僵了,有的生了冻疮,握不住写字的铅笔,只得时常捧手呵气。脚趾头也冻麻了,教室里时常传来同学们双脚踏地的声音。好不容易熬过一节课,传来下课的铃声,老师一句“下课”,学生们从教室鱼贯而出。男同学扎堆取暖,一个个依次倚朝阳的一面墙壁用力往前面挤,不时声声地喊着:“哎唷!哎唷!”女同学主要是玩踢毽子的游戏,有时也相互追逐嬉闹。课间十分钟,实际上是活动取暖的时间。
我读的小学,是当时大队办的一所学校,离家有二里路,路上两边是空旷的农田。初办时设在一所老旧的庙宇里,叫“天王殿”,“破四旧”时,寺院改成了学校。后来大队为了改善办学条件,在庙宇旁边又新盖了七八间简易的砖瓦房,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在那里读的小学。当时,学校没有食堂,无力提供午餐,老师和学生都是回家吃饭。碰到冰冻雨雪天,父亲会顶风冒雪拎着篮子,送午饭过来,让我们在路上少受点寒冷。
放学回家后,最想亲近的是火熜。那是取暖神器,黄铜铸造的,有多眼的盖,还有提梁,可以拎着四处行走。里面烧的是砻糠或锯末,铲上没有烧透的棉花杆的红灰盖在上面,引着砻糠或锯末,冒一阵烟,烟尽了,就可以盖上盖。砻糠和锯末慢慢延烧,有时砻糠太实了,火力渐微,就要用“拨火板”沿边上挖两下,把砻糠拨松,火就旺了。先烘烘手,再暖暖脚,脚暖则全身暖。全身暖和了,就想着弄点吃的。从豆瓮里取来一把倭豆,掀起火熜盖,拨开表面的暗灰,将倭豆一粒一粒煨着,不一会,倭豆发出“扑扑”的声音,赶紧翻个面,散发出的香味,真诱人。在食物稀缺的年代,炒倭豆是农家常见的最好吃的零食。火熜,小孩需要,老人更离不开。我家里有两只火熜,一只归爷爷专用,年纪大了,怕冷,白天黑夜火熜不离身,见我们放学回家,招呼我们围着他烘烘手,把煨好的年糕分给我们。傍晚时分,母亲准备淘米做饭,我最乐意干的家务活,就是跑到灶间生火烧饭,坐在小板凳,轻松地往镬洞里添着柴草,火光映红了我的脸庞,浑身暖和。